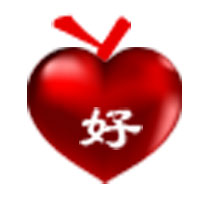信息来源:兴化日报 发布日期:2023-06-30
漂泊在外,心心念念古镇的烟火气。
东码头清冷空荡。透过晨雾,隐约可见河对岸,傍水而建的一幢瓦屋冒出一缕缕炊烟。古镇很少有人家烧柴草了,保留的烟囱大多形同虚设。偶尔看到的炊烟,会让人倍感亲切和温暖,瞬间有种穿越的感觉。
几十年前,古镇最热闹的地方无疑是东码头。开门见水、出门坐船的水乡,码头是人们通向外面的驿站,这里的客货两用的帮船有好几家:去安丰的、去沙沟的、去兴化的。每天,码头上停满了外来的商船、运输船、打渔船等等。中午时分,船上生火做饭,一道道白色的炊烟,像一方方白色的头巾,齐刷刷地升到上空。
暮色降临,喧闹了一个白天的古镇逐渐安静下来,河面上剩下几点渔火。太阳还没有升起,东方已有一丝光亮,挑水人起床了,空气里弥漫着破晓时的寒气。沉淀了一夜的渭水河比什么时候都要清澈,挑水的彼此打着招呼,肩头是沉重的水桶还有同样沉重的日子。古镇曾有专门的挑水工,给大户人家或者浴室挑水。2分钱一担水,延续了多年的工钱标准。夏天用水量大,挑水工套上坎肩,脖子上挂一条擦汗的毛巾,穿上草鞋,步子平稳轻快。浴室老板招挑水工要求苛刻:步履轻快而且桶里的水不允许溅洒出来。
沿着码头拾级而上,是东西向的双溪路。当年,一条青石板铺就的道路把青砖黛瓦的房子分成南北两个部分,这里聚集了古镇的店铺商行。卖柴米油盐的,卖日用百货的,甚至有卖小猪崽的。如果“逢集”,周边乡镇的人都会赶来,你挤着我,我挤着你,叫卖声此起彼伏。“行老板”们在人群里穿梭着,作为做生意的中间人,他们用大杆秤和信誉保证着每一桩交易的不偏不倚与公平公正。
古镇早茶文化兴盛。晨光熹微,就有人安坐在早茶店里,泡一壶浓茶,要一碟干丝生姜,开始享受生活。干丝吃完了,再来一两个包子或者一碗阳春面。大街上曾经有两家赫赫有名的饭店:东饭店、西饭店。相对来说,西饭店的名气和规模更大一些。开源饭店的小碗子,曾是东饭店的顶梁柱,擅长做点心,蟹黄包和翡翠烧卖是她的拿手绝活。古镇人结婚过生日,常请小碗子去掌勺。生活和岁月同时压弯了小碗子的腰,愿赌服输的她早把手艺和饭店同时交给了儿子。儿子厚道,饭店生意红火。面条是西饭店的招牌,大锅、肉汤,是它的秘密。煮好的面条放到肉汤前必须把水沥干。物质匮乏的时代,母亲常让我持大瓷缸去买碗面条。9分钱,2两粮票。在我央求下,下面条的阿姨总是尽可能地多放几勺肉汤。
米摊饼摊子总是抢在太阳出来前上街,摆在了老书店旁边,几十年了,还是那个位置。锅腔刚一放下,有人就围了上来。男人烧火,女人做饼。烧的是芦柴,便于掌握火候。干燥的芦柴,火柴一划,腾地就着了。有人计算过,平均下来,一锅饼三分钟,一锅十二个。米摊饼宜趁热吃。包油条是绝配,镇上人喜欢成全它们。黄烧饼的顾客比较固定,就像它固定而笨重的炉子一样。它烧炭。做饼师傅有点驼背,但丝毫不影响做饼的速度。酥脆香甜的烧饼,轻咬一口,碎屑四下逃散,香气四溢,像飘落的桂花,满大街都能闻见。
黄烧饼常常进城,还有馓葽子。馓葽子做得好,“盘条”很重要。盘条先和面,考验臂力和耐力。面和好后,搓成拇指粗的长条,必须粗细均匀,盘放在一个大盆子里。主人用香油均匀浇在“黄鳝”上,不让它粘连。这个时候,长条似一条听话的黄鳝,温温顺顺地曲着身子。炸时,把“黄鳝”放在手上缠绕,抻长,最后用长长的竹筷支到翻滚的油锅里。以前,古镇有给产妇送月子礼的规矩:一包红糖、二斤猪肉、二十个黄烧饼加上四斤馓葽子。
古镇的熏烧摊不缺顾客。劳碌了一天的古镇人喜欢用烧酒刺激自己。熏烧是最好的下酒菜,特别是猪头肉,肉色泽红润,肥而不腻,入口即化,绝对是古镇酒徒的福音。我小学同学,现在的东饭店王老板,很会“享受”。傍晚打烊,他总喜欢犒赏下自己:一大杯白酒,一碟花生米和一盘猪头肉。王同学沐浴着东码头的清风,哼着不知名的小调,喝着吃着,醉意朦胧后一觉天亮。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。
冬天,轰米花的忙碌了。大街中心老书店的电线杆下,是轰米花的张老伯“地盘”。老人戴一顶旧军帽,时不时摘下来掸掸灰尘。生意一来,张老伯便脱去外面的棉袄,露出淡蓝色的中山装。炉子里蹿着蓝色火焰,张老伯一手拉着风箱,一手摇着圆滚滚的黑锅。“得罪,让下!”张老伯把锅口对准麻袋上方的皮圈,用一根铁撬杠插进锅口阀门的开关上,用力一扳,轰的一声,麻袋猛地鼓胀起来,地上腾起一层白色烟雾。一群小孩蜂拥而上。
说书的孙汉文大爷住在虹桥西巷。古镇的孩子曾趋之若鹜,挤满了他家的堂屋。缠着脚的孙奶奶,总是好奇地望着我们这群孩子。孙大爷胖胖的,怕热,上身穿着背心,弥陀佛一般,手里抓着大蒲扇,讲《岳飞传》、讲《杨家将》,总把我们的胃口调起来后又戛然而止,我们只能第二天再去。孙大爷说书时,院子里鸦雀无声。可以说,现代的课堂,很难有这样的景象了。现在,虹桥西巷没有了说书人,也没有了听书的人。当年听书的孩子早已成了爷爷。
没有人统计过古镇有多少种职业的手艺人,太多了:刻章的、开锁的、修鞋的、补锅的、剃头的、开脸的、修钟表的、做秤的、做糖果的、修单车的、编篮子的、修钢笔的、敲白铁皮的、弹棉花的。三百六十行,行行出状元。每个手艺人都对自己的手艺有一种近乎自负的自尊。技有高低,业无贵贱。做手艺的,本质上一样,靠双手劳动、凭手艺吃饭。手艺人聪明敏感,这些人里诞生了古镇第一批下海经商的人,卖衣服、卖鞋子、卖百货。他们赚到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桶金后,不少去了城里发展。现在的大街上,除了修鞋的剃头的等极少数手艺人还干着老本行外,其余的都成了“非遗”。
古镇人有的是时间和闲情,适合打麻将。大街上,侧耳一听,全是麻将洗牌声。雨天是赌钱的最好时间,雨声掩盖了哗哗的搓牌声。没有麻将的长假是无趣的。在外面赚回的钱,不在牌桌上显摆一下,如锦衣夜行。人生如牌场,洗牌、码牌、打牌,落子无悔,牌桌上没有永远的赢家。大家越来越感到,靠双手赚来的钱比在桌上赢的钱靠谱得多。于是,他们干脆戒了赌,溜到“市民广场”,伴着音乐,用欢快的舞步,证明着日子的富足和安闲。
贫穷始终是古镇的敌人。为了改变命运,古镇走出去的人越来越多。你不要担心走出去的他们靠什么活着,生命自有生命的出路,只要有一双能吃苦耐劳的手。他们做生意、跑外卖,跑运输、在工厂打工……什么赚到钱干什么。每个在外的古镇人,都有一段与命运相搏的故事。城市坚硬,古镇柔软。在城市拼累了,他们就回到古镇,在慢生活里寻找初心。生命是一株植物,从苍翠到衰老,不显山也不露水。回到古镇时,他们才发现,岁月的刀子已经把他们砍削得面目全非。太阳每天升起,但时光不会倒流。
古镇的兴盛和衰败,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。古镇最大的邹氏家族其实也不是原住民,是明初从苏州阊门迁徙而来。“年深外境犹吾境,身在他乡即故乡”,几百年繁衍生息,这里早已成了他们的故乡。
古镇人的眼里,老家就是一个又一个平常的日子,吃喝拉撒、柴米油盐还有人情世故。这是古镇延续了几百年的烟火气、精气神,也是留给古镇游子的慰藉和念想。古镇在兴化的最北面,和盐都区隔河相望,因邹姓居多,取名大邹。
每一位大邹人都怀揣着一本关于家乡的词典:米摊饼、黄烧饼、猪头肉、大码头、西饭店……这些词汇,烟火味十足,他们如数家珍——尽管不少已经被时代的河流淹没,消失在岁月深处,找寻不见……
那些找寻不见的,都是乡愁。